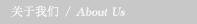韩美林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
韩美林:通过我们工作室二十八年做了58所巨型雕塑的实践经验:我们必须要来讨论现在这个“公共空间”的问题。因为中华民族现在正处在往上升的一个时代,我认为应该讲实话了。
我举个例子:我们曾经给芜湖市委做了一个雕塑,当时雕塑所在地的周边包括芜湖市政府、市委和居民全搬光了。这么大的一个雕塑,做的也不错,大家都很欢迎,可是没想到过几天雕塑周边的高楼都起来了。比如,广播电台、妇产二院等,楼上面都是很大的大红字,结果把我们雕塑包得就剩了这么小了。事实上是因为公共环境没有人设计,这就是设计院的问题,是协调规划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又不是。刚才朋友们也说了,是甲乙方的问题,你说这么做,他就不这么做,因为我有权,这就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这里面又产生了矛盾,你说听不听?像这种关系,我认为在这个前进的时代有必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钱绍武先生给我的鼓励,我永远敬重这样的老师,他给我使劲让我向前进。他并不是站在我的角度,他是站在时代的角度看待艺术,艺术应该前进。
所以,我认为客观环境必须打开,这并不仅是主观的问题,不仅是艺术家的艺术问题,也是他的艺术能否存在的问题。我们在1989年做大连老虎滩大型雕塑的时候,一共六只花岗岩大老虎,有人还没看到雕塑落成就到上头去打小报告,说韩美林做了一窝黄鼠狼,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老虎滩的雕塑规模,六只老虎总长度达42米。最终因人为的干涉,雕塑停工9个月,钱也不给我们,后来我站在老虎的头上大哭,我说我报国无门。停工9个月后,有一位领导说美林你偷着做,我们就偷着做。最终老虎雕塑做成功了,而那个当时打报告的人竟然在领导人面前谄媚当时他是多么支持韩美林的。这里其实就是审美观不够、文化修养不高、艺术修养不够,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今天,正好有好多奥组委的老朋友都在这儿,我就谈谈在设计福娃的过程中,韩美林做到了什么程度?无论是政治(斗争)也好,还是经济(斗争)也好,文化斗争是更隐秘、更长远的一种斗争。政治斗争谁把谁弄下去是看不见的,谁把谁弄上来是能看得见的。而文化斗争可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设计的福娃还没出稿前,他们有些人擅自选定的是这个(展示一张设计稿,“拨浪鼓”形象),我们吉祥物要是它的话丢人不丢人?同志们,这是熊猫(展示一张设计稿),这是猴子(展示一张设计稿)。那些人时时干涉、刁难我,在我们设计过程中指指点点,就是不报送我们这五个娃,如果最后福娃选定的是这只熊猫和猴子,我非气得跳河不行。为什么?因为出了问题是韩美林的,韩美林是设计组长。
后来,我把五个娃拿到中央领导人那儿,中央领导人说,“根本没看到这五个娃,他们这么漂亮,你来的正是时候,明天中央开会就讨论吉祥物的问题。”中央领导人曾经说过,韩美林要是到这儿来可以给他开“绿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绿灯”,直接把这五个娃拿过去。最终,这五个娃才出来的。这件事情的真相和我所受到的压力,包含奥组委领导,在座的奥组委的朋友们,还有常沙娜老师都很了解。
我只想说,同志们,那些个人主义的艺术观和审美能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吗?
所以,我认为,为了我们的民族和民族的尊严,我们不能在艺术上落后、在文化上落后,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进,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繁荣。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尽一点力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白岩松(主持人):其实美林的这番演讲一如他的一贯风格,直率、坦诚,政协会上人家就说,那么多委员正在那儿讲话呢,他给人打断了,“咱到这儿是献计献策的,不是献媚的。”艺术家面临的挑战,在全世界哪儿都有。我在佛罗伦萨听到的,米开朗基罗大卫雕塑,那个时候也不开放,很多宗教的领导过来审这个雕塑,“不行,这个脑门必须改。”米开朗基罗说,“我改,马上改。”他拿着雕刻刀上去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把石膏粉,他上去一边用雕刻刀“凿”,一边让手里的石膏粉哗哗地往下撒,然后这一把粉全撒完了,用手一抹,修完了,那个领导看着说,“改完了好多了”。所以,不仅需要韩美林这种直抒胸襟来改造我们的环境,也需要有的时候拥有一种韧性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今天“韩美林日”所传播的思想:通过教育,通过大家对审美观的改变,让大家的生活“与美为邻”,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机构审批后,变得跟众多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样,甚至比传统的还不好。让一群三流的眼光去改一个大师的作品,结果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如三流水平的东西。
所以,商业的力量、意识形态和不当的管理体制,将会对我们的公共审美造成伤害,我希望这种伤害尽快成为历史。谢谢!

韩美林